萨埵之歌
遇见莲以前,她只会抚琴微笑。她不会弹琴,她甚至分不清哪一个是商音。站在台上唱那些自说愁的歌曲,穿着华贵的衣裳,摆弄自己的肢首。如此冷漠微寒的衣袂,躲藏在这堂皇的景色中,格格不入,的孤独。
还未及笄,心便已开始老去。
遇见莲那天,她恐惧地不知所措。莲站在高大的棕色宝马上,穿着饱满的黑色灯笼裤,黑色短马甲,黑色护腕,黑色布鞋,黑色的斗篷被风吹扬,黑色的瞳孔啸成剑气,黑色的发乱成不羁的形状。她从未见过这么轻视死亡的人,而莲,是第一个。反着光的马孙刀颀长,将生命分成过去和现在两段,轻易地刺死了生命的未来。
鲜血溅起来,乱发下莲的笑容,那样意气风发。
那一刻,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变成那马孙刀下起舞的亡魂,在最近的距离看清莲嘲讽般的笑容,散发着毁灭世界的诡异气息,又洋溢着救世主般的孤傲,和居高临下。
莲看她时是居高临下的,马孙刀挑起她的下颔,刀刃清澈反射出她下颔的轮廓,划过时切断她耳旁落下的碎发。
从那一刻开始她如此地讨厌自己。莲皱着眉,鄙夷地说:“女人。”
她本来也是不喜欢女人的,她也希望自己是个男儿身。而这两个字冰冷得打掉她所有生存的臆想,深沉而且,绝望。
道莲。她念这两个字时很用力,少年回头,看不见她藏在阴影中的表情。
凯达格兰大道上教堂传出虔诚的歌声,唱诗班的孩子穿素色的衣服,闭眼着赞颂上帝。纯色皮肤上朵朵天真,张眼眸子里写满沧桑。
是不是会有面包和方糖,和着咖啡在阳光慵懒的午后,细享?而又要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“人”,是不是必须像该隐一样站起来挥舞盾和长枪?甚至无法透析生命的目的,是不是只为刺穿空气上端暧昧不清的欲望?
没有人回答,亦没有人听到我的声响。
白鸽被工业浓厚的气味熏得灰黑,飞行中只有眼睛像鸢尾花的光芒。咽下的是希望,曲水流觞。
心中的皱褶似蝴蝶,为了谁,折了翼。
那样一个似幻非幻的世界,所有烟火都踏在历史的纹理中,人们在梦中惊魇或深呓,没有什么可以成为阻止时间前进的绊脚石,甚至死亡。于是有了上帝与朝圣者,有了伯爵与吸血鬼,有了天使与加百利,有了恶魔与路西法。
开膛手杰克的枪口窜出轻烟淡淡,世界不相信,世界。
她也念《古兰经》,她也信伊斯兰,她也用没有重低音炮的音响放摇滚,她也在看悲情肥皂剧时吃苍蝇小店送来的快餐。她同样也会反复诵读爱人的名字,再簇上前闻闻花开的静然。
喜欢青色,那种生机盎然的颜色,牵着时间万物的消长,奔赴一场奭大的死亡。
寂寞挡在眼前如横亘,夭夭冶用灰色作光芒。她翘着腿撅着嘴路过那些灵敏而平凡的生命时,她会骄傲地仰起脸。他是英雄。他是我丈夫。
他是英雄。硬扯着烟缁色的笑容,勇猛地用身体抵抗,抵抗了些什么,也许不过是心中一些幼稚而纯洁的幻想。他听见风呼啦啦地吹,遍体鳞伤地穿过荆棘,于是他便拿自己的身体,呼啦啦地强穿敌人的炮火封锁线。
风遍体鳞伤,他也遍体鳞伤。
风长啸一声,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狂奔,他也长啸一声,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狂奔。
他不是风。所以风穿透了敌人的铠甲,而他,必须倒下。
烈士铭碑上他的名字排在榜首,她微笑,然后泪如雨下。
这便是他承诺给她的整个世界,用名誉,和血。
盛唐之时不允许有这样的嗜血魔,道家的地方独裁渐渐被人们憎恨,她也再没见过莲。她常常会想那个如此气傲的家伙是不是还会站在巨马上,斗篷翻飞,瞳中燃起焚烧三界的红莲之火,那样纯粹,那样悲悯。所过之处,皆为修罗场,腥涩的甜味铺天盖地散开去,无边无际。
亦无法无天。
想到这里她会吃吃地笑,莲不是这般恶魔的人罢,呵呵,这是不是自己梦中的自己呢?
她一直便不喜欢女儿身,她想成为男儿上阵,燕然勒功,然后醉尸沙场,从此酣睡在被血液浸湿的土地上,看飞扬的旌旗如何如何华美,也看闪光的旄钺如何如何锋利,看摇摆的马鬣如何如何狭长。
有时她会痛恨自己为什么这么血腥,于是裹一身黑氅佯装黑无常,拿起铁索,撇下八字眉,用死亡代替一切语短言长。
笑声如银铃,她说,我只是想离开。
或问,去哪里?
答曰,奔赴幕上梦想。
“出鞘剑,杀气荡,风起无月的战场。
千军万马独身闯,一身是胆好儿郎。
儿女情,前世帐,你的笑活着怎么忘。
美人泪,断人肠,这能取人性命是胭脂烫。”
拾阶而上,裙裾上盛开大朵大朵的珍珠和年华,发迹垂下几斛琅玕,几迭团扇。
“诀别诗,两三行。
写在三月春雨的路上,若我能,遇见莲以前,她只会抚琴微笑。她不会弹琴,她甚至分不清哪一个是商音。站在台上唱那些自说愁的歌曲,穿着华贵的衣裳,摆弄自己的肢首。如此冷漠微寒的衣袂,躲藏在这堂皇的景色中,格格不入,的孤独。
还未及笄,心便已开始老去。
遇见莲那天,她恐惧地不知所措。莲站在高大的棕色宝马上,穿着饱满的黑色灯笼裤,黑色短马甲,黑色护腕,黑色布鞋,黑色的斗篷被风吹扬,黑色的瞳孔啸成剑气,黑色的发乱成不羁的形状。她从未见过这么轻视死亡的人,而莲,是第一个。反着光的马孙刀颀长,将生命分成过去和现在两段,轻易地刺死了生命的未来。
鲜血溅起来,乱发下莲的笑容,那样意气风发。
那一刻,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变成那马孙刀下起舞的亡魂,在最近的距离看清莲嘲讽般的笑容,散发着毁灭世界的诡异气息,又洋溢着救世主般的孤傲,和居高临下。
莲看她时是居高临下的,马孙刀挑起她的下颔,刀刃清澈反射出她下颔的轮廓,划过时切断她耳旁落下的碎发。
从那一刻开始她如此地讨厌自己。莲皱着眉,鄙夷地说:“女人。”
她本来也是不喜欢女人的,她也希望自己是个男儿身。而这两个字冰冷得打掉她所有生存的臆想,深沉而且,绝望。
道莲。她念这两个字时很用力,少年回头,看不见她藏在阴影中的表情。
凯达格兰大道上教堂传出虔诚的歌声,唱诗班的孩子穿素色的衣服,闭眼着赞颂上帝。纯色皮肤上朵朵天真,张眼眸子里写满沧桑。
是不是会有面包和方糖,和着咖啡在阳光慵懒的午后,细享?而又要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“人”,是不是必须像该隐一样站起来挥舞盾和长枪?甚至无法透析生命的目的,是不是只为刺穿空气上端暧昧不清的欲望?
没有人回答,亦没有人听到我的声响。
白鸽被工业浓厚的气味熏得灰黑,飞行中只有眼睛像鸢尾花的光芒。咽下的是希望,曲水流觞。
心中的皱褶似蝴蝶,为了谁,折了翼。
那样一个似幻非幻的世界,所有烟火都踏在历史的纹理中,人们在梦中惊魇或深呓,没有什么可以成为阻止时间前进的绊脚石,甚至死亡。于是有了上帝与朝圣者,有了伯爵与吸血鬼,有了天使与加百利,有了恶魔与路西法。
开膛手杰克的枪口窜出轻烟淡淡,世界不相信,世界。
她也念《古兰经》,她也信伊斯兰,她也用没有重低音炮的音响放摇滚,她也在看悲情肥皂剧时吃苍蝇小店送来的快餐。她同样也会反复诵读爱人的名字,再簇上前闻闻花开的静然。
喜欢青色,那种生机盎然的颜色,牵着时间万物的消长,奔赴一场奭大的死亡。
寂寞挡在眼前如横亘,夭夭冶用灰色作光芒。她翘着腿撅着嘴路过那些灵敏而平凡的生命时,她会骄傲地仰起脸。他是英雄。他是我丈夫。
他是英雄。硬扯着烟缁色的笑容,勇猛地用身体抵抗,抵抗了些什么,也许不过是心中一些幼稚而纯洁的幻想。他听见风呼啦啦地吹,遍体鳞伤地穿过荆棘,于是他便拿自己的身体,呼啦啦地强穿敌人的炮火封锁线。
风遍体鳞伤,他也遍体鳞伤。
风长啸一声,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狂奔,他也长啸一声,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狂奔。
他不是风。所以风穿透了敌人的铠甲,而他,必须倒下。
烈士铭碑上他的名字排在榜首,她微笑,然后泪如雨下。
这便是他承诺给她的整个世界,用名誉,和血。
盛唐之时不允许有这样的嗜血魔,道家的地方独裁渐渐被人们憎恨,她也再没见过莲。她常常会想那个如此气傲的家伙是不是还会站在巨马上,斗篷翻飞,瞳中燃起焚烧三界的红莲之火,那样纯粹,那样悲悯。所过之处,皆为修罗场,腥涩的甜味铺天盖地散开去,无边无际。
亦无法无天。
想到这里她会吃吃地笑,莲不是这般恶魔的人罢,呵呵,这是不是自己梦中的自己呢?
她一直便不喜欢女儿身,她想成为男儿上阵,燕然勒功,然后醉尸沙场,从此酣睡在被血液浸湿的土地上,看飞扬的旌旗如何如何华美,也看闪光的旄钺如何如何锋利,看摇摆的马鬣如何如何狭长。
有时她会痛恨自己为什么这么血腥,于是裹一身黑氅佯装黑无常,拿起铁索,撇下八字眉,用死亡代替一切语短言长。
笑声如银铃,她说,我只是想离开。
或问,去哪里?
答曰,奔赴幕上梦想。
“出鞘剑,杀气荡,风起无月的战场。
千军万马独身闯,一身是胆好儿郎。
儿女情,前世帐,你的笑活着怎么忘。
美人泪,断人肠,这能取人性命是胭脂烫。”
拾阶而上,裙裾上盛开大朵大朵的珍珠和年华,发迹垂下几斛琅玕,几迭团扇。
“诀别诗,两三行。
写在三月春雨的路上,若我能,遇见莲以前,她只会抚琴微笑。她不会弹琴,她甚至分不清哪一个是商音。站在台上唱那些自说愁的歌曲,穿着华贵的衣裳,摆弄自己的肢首。如此冷漠微寒的衣袂,躲藏在这堂皇的景色中,格格不入,的孤独。
还未及笄,心便已开始老去。
遇见莲那天,她恐惧地不知所措。莲站在高大的棕色宝马上,穿着饱满的黑色灯笼裤,黑色短马甲,黑色护腕,黑色布鞋,黑色的斗篷被风吹扬,黑色的瞳孔啸成剑气,黑色的发乱成不羁的形状。她从未见过这么轻视死亡的人,而莲,是第一个。反着光的马孙刀颀长,将生命分成过去和现在两段,轻易地刺死了生命的未来。
鲜血溅起来,乱发下莲的笑容,那样意气风发。
那一刻,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变成那马孙刀下起舞的亡魂,在最近的距离看清莲嘲讽般的笑容,散发着毁灭世界的诡异气息,又洋溢着救世主般的孤傲,和居高临下。
莲看她时是居高临下的,马孙刀挑起她的下颔,刀刃清澈反射出她下颔的轮廓,划过时切断她耳旁落下的碎发。
从那一刻开始她如此地讨厌自己。莲皱着眉,鄙夷地说:“女人。”
她本来也是不喜欢女人的,她也希望自己是个男儿身。而这两个字冰冷得打掉她所有生存的臆想,深沉而且,绝望。
道莲。她念这两个字时很用力,少年回头,看不见她藏在阴影中的表情。
凯达格兰大道上教堂传出虔诚的歌声,唱诗班的孩子穿素色的衣服,闭眼着赞颂上帝。纯色皮肤上朵朵天真,张眼眸子里写满沧桑。
是不是会有面包和方糖,和着咖啡在阳光慵懒的午后,细享?而又要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“人”,是不是必须像该隐一样站起来挥舞盾和长枪?甚至无法透析生命的目的,是不是只为刺穿空气上端暧昧不清的欲望?
没有人回答,亦没有人听到我的声响。
白鸽被工业浓厚的气味熏得灰黑,飞行中只有眼睛像鸢尾花的光芒。咽下的是希望,曲水流觞。
心中的皱褶似蝴蝶,为了谁,折了翼。
那样一个似幻非幻的世界,所有烟火都踏在历史的纹理中,人们在梦中惊魇或深呓,没有什么可以成为阻止时间前进的绊脚石,甚至死亡。于是有了上帝与朝圣者,有了伯爵与吸血鬼,有了天使与加百利,有了恶魔与路西法。
开膛手杰克的枪口窜出轻烟淡淡,世界不相信,世界。
她也念《古兰经》,她也信伊斯兰,她也用没有重低音炮的音响放摇滚,她也在看悲情肥皂剧时吃苍蝇小店送来的快餐。她同样也会反复诵读爱人的名字,再簇上前闻闻花开的静然。
喜欢青色,那种生机盎然的颜色,牵着时间万物的消长,奔赴一场奭大的死亡。
寂寞挡在眼前如横亘,夭夭冶用灰色作光芒。她翘着腿撅着嘴路过那些灵敏而平凡的生命时,她会骄傲地仰起脸。他是英雄。他是我丈夫。
他是英雄。硬扯着烟缁色的笑容,勇猛地用身体抵抗,抵抗了些什么,也许不过是心中一些幼稚而纯洁的幻想。他听见风呼啦啦地吹,遍体鳞伤地穿过荆棘,于是他便拿自己的身体,呼啦啦地强穿敌人的炮火封锁线。
风遍体鳞伤,他也遍体鳞伤。
风长啸一声,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狂奔,他也长啸一声,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狂奔。
他不是风。所以风穿透了敌人的铠甲,而他,必须倒下。
烈士铭碑上他的名字排在榜首,她微笑,然后泪如雨下。
这便是他承诺给她的整个世界,用名誉,和血。
盛唐之时不允许有这样的嗜血魔,道家的地方独裁渐渐被人们憎恨,她也再没见过莲。她常常会想那个如此气傲的家伙是不是还会站在巨马上,斗篷翻飞,瞳中燃起焚烧三界的红莲之火,那样纯粹,那样悲悯。所过之处,皆为修罗场,腥涩的甜味铺天盖地散开去,无边无际。
亦无法无天。
想到这里她会吃吃地笑,莲不是这般恶魔的人罢,呵呵,这是不是自己梦中的自己呢?
她一直便不喜欢女儿身,她想成为男儿上阵,燕然勒功,然后醉尸沙场,从此酣睡在被血液浸湿的土地上,看飞扬的旌旗如何如何华美,也看闪光的旄钺如何如何锋利,看摇摆的马鬣如何如何狭长。
有时她会痛恨自己为什么这么血腥,于是裹一身黑氅佯装黑无常,拿起铁索,撇下八字眉,用死亡代替一切语短言长。
笑声如银铃,她说,我只是想离开。
或问,去哪里?
答曰,奔赴幕上梦想。
“出鞘剑,杀气荡,风起无月的战场。
千军万马独身闯,一身是胆好儿郎。
儿女情,前世帐,你的笑活着怎么忘。
美人泪,断人肠,这能取人性命是胭脂烫。”
拾阶而上,裙裾上盛开大朵大朵的珍珠和年华,发迹垂下几斛琅玕,几迭团扇。
“诀别诗,两三行。
写在三月春雨的路上,若我能,遇见莲以前,她只会抚琴微笑。她不会弹琴,她甚至分不清哪一个是商音。站在台上唱那些自说愁的歌曲,穿着华贵的衣裳,摆弄自己的肢首。如此冷漠微寒的衣袂,躲藏在这堂皇的景色中,格格不入,的孤独。
还未及笄,心便已开始老去。
遇见莲那天,她恐惧地不知所措。莲站在高大的棕色宝马上,穿着饱满的黑色灯笼裤,黑色短马甲,黑色护腕,黑色布鞋,黑色的斗篷被风吹扬,黑色的瞳孔啸成剑气,黑色的发乱成不羁的形状。她从未见过这么轻视死亡的人,而莲,是第一个。反着光的马孙刀颀长,将生命分成过去和现在两段,轻易地刺死了生命的未来。
鲜血溅起来,乱发下莲的笑容,那样意气风发。
那一刻,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变成那马孙刀下起舞的亡魂,在最近的距离看清莲嘲讽般的笑容,散发着毁灭世界的诡异气息,又洋溢着救世主般的孤傲,和居高临下。
莲看她时是居高临下的,马孙刀挑起她的下颔,刀刃清澈反射出她下颔的轮廓,划过时切断她耳旁落下的碎发。
从那一刻开始她如此地讨厌自己。莲皱着眉,鄙夷地说:“女人。”
她本来也是不喜欢女人的,她也希望自己是个男儿身。而这两个字冰冷得打掉她所有生存的臆想,深沉而且,绝望。
道莲。她念这两个字时很用力,少年回头,看不见她藏在阴影中的表情。
凯达格兰大道上教堂传出虔诚的歌声,唱诗班的孩子穿素色的衣服,闭眼着赞颂上帝。纯色皮肤上朵朵天真,张眼眸子里写满沧桑。
是不是会有面包和方糖,和着咖啡在阳光慵懒的午后,细享?而又要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“人”,是不是必须像该隐一样站起来挥舞盾和长枪?甚至无法透析生命的目的,是不是只为刺穿空气上端暧昧不清的欲望?
没有人回答,亦没有人听到我的声响。
白鸽被工业浓厚的气味熏得灰黑,飞行中只有眼睛像鸢尾花的光芒。咽下的是希望,曲水流觞。
心中的皱褶似蝴蝶,为了谁,折了翼。
那样一个似幻非幻的世界,所有烟火都踏在历史的纹理中,人们在梦中惊魇或深呓,没有什么可以成为阻止时间前进的绊脚石,甚至死亡。于是有了上帝与朝圣者,有了伯爵与吸血鬼,有了天使与加百利,有了恶魔与路西法。
开膛手杰克的枪口窜出轻烟淡淡,世界不相信,世界。
她也念《古兰经》,她也信伊斯兰,她也用没有重低音炮的音响放摇滚,她也在看悲情肥皂剧时吃苍蝇小店送来的快餐。她同样也会反复诵读爱人的名字,再簇上前闻闻花开的静然。
喜欢青色,那种生机盎然的颜色,牵着时间万物的消长,奔赴一场奭大的死亡。
寂寞挡在眼前如横亘,夭夭冶用灰色作光芒。她翘着腿撅着嘴路过那些灵敏而平凡的生命时,她会骄傲地仰起脸。他是英雄。他是我丈夫。
他是英雄。硬扯着烟缁色的笑容,勇猛地用身体抵抗,抵抗了些什么,也许不过是心中一些幼稚而纯洁的幻想。他听见风呼啦啦地吹,遍体鳞伤地穿过荆棘,于是他便拿自己的身体,呼啦啦地强穿敌人的炮火封锁线。
风遍体鳞伤,他也遍体鳞伤。
风长啸一声,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狂奔,他也长啸一声,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狂奔。
他不是风。所以风穿透了敌人的铠甲,而他,必须倒下。
烈士铭碑上他的名字排在榜首,她微笑,然后泪如雨下。
这便是他承诺给她的整个世界,用名誉,和血。
盛唐之时不允许有这样的嗜血魔,道家的地方独裁渐渐被人们憎恨,她也再没见过莲。她常常会想那个如此气傲的家伙是不是还会站在巨马上,斗篷翻飞,瞳中燃起焚烧三界的红莲之火,那样纯粹,那样悲悯。所过之处,皆为修罗场,腥涩的甜味铺天盖地散开去,无边无际。
亦无法无天。
想到这里她会吃吃地笑,莲不是这般恶魔的人罢,呵呵,这是不是自己梦中的自己呢?
她一直便不喜欢女儿身,她想成为男儿上阵,燕然勒功,然后醉尸沙场,从此酣睡在被血液浸湿的土地上,看飞扬的旌旗如何如何华美,也看闪光的旄钺如何如何锋利,看摇摆的马鬣如何如何狭长。
有时她会痛恨自己为什么这么血腥,于是裹一身黑氅佯装黑无常,拿起铁索,撇下八字眉,用死亡代替一切语短言长。
笑声如银铃,她说,我只是想离开。
或问,去哪里?
答曰,奔赴幕上梦想。
“出鞘剑,杀气荡,风起无月的战场。
千军万马独身闯,一身是胆好儿郎。
儿女情,前世帐,你的笑活着怎么忘。
美人泪,断人肠,这能取人性命是胭脂烫。”
拾阶而上,裙裾上盛开大朵大朵的珍珠和年华,发迹垂下几斛琅玕,几迭团扇。
“诀别诗,两三行。
写在三月春雨的路上,若我能,遇见莲以前,她只会抚琴微笑。她不会弹琴,她甚至分不清哪一个是商音。站在台上唱那些自说愁的歌曲,穿着华贵的衣裳,摆弄自己的肢首。如此冷漠微寒的衣袂,躲藏在这堂皇的景色中,格格不入,的孤独。
还未及笄,心便已开始老去。
遇见莲那天,她恐惧地不知所措。莲站在高大的棕色宝马上,穿着饱满的黑色灯笼裤,黑色短马甲,黑色护腕,黑色布鞋,黑色的斗篷被风吹扬,黑色的瞳孔啸成剑气,黑色的发乱成不羁的形状。她从未见过这么轻视死亡的人,而莲,是第一个。反着光的马孙刀颀长,将生命分成过去和现在两段,轻易地刺死了生命的未来。
鲜血溅起来,乱发下莲的笑容,那样意气风发。
那一刻,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变成那马孙刀下起舞的亡魂,在最近的距离看清莲嘲讽般的笑容,散发着毁灭世界的诡异气息,又洋溢着救世主般的孤傲,和居高临下。
莲看她时是居高临下的,马孙刀挑起她的下颔,刀刃清澈反射出她下颔的轮廓,划过时切断她耳旁落下的碎发。
从那一刻开始她如此地讨厌自己。莲皱着眉,鄙夷地说:“女人。”
她本来也是不喜欢女人的,她也希望自己是个男儿身。而这两个字冰冷得打掉她所有生存的臆想,深沉而且,绝望。
道莲。她念这两个字时很用力,少年回头,看不见她藏在阴影中的表情。
凯达格兰大道上教堂传出虔诚的歌声,唱诗班的孩子穿素色的衣服,闭眼着赞颂上帝。纯色皮肤上朵朵天真,张眼眸子里写满沧桑。
是不是会有面包和方糖,和着咖啡在阳光慵懒的午后,细享?而又要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“人”,是不是必须像该隐一样站起来挥舞盾和长枪?甚至无法透析生命的目的,是不是只为刺穿空气上端暧昧不清的欲望?
没有人回答,亦没有人听到我的声响。
白鸽被工业浓厚的气味熏得灰黑,飞行中只有眼睛像鸢尾花的光芒。咽下的是希望,曲水流觞。
心中的皱褶似蝴蝶,为了谁,折了翼。
那样一个似幻非幻的世界,所有烟火都踏在历史的纹理中,人们在梦中惊魇或深呓,没有什么可以成为阻止时间前进的绊脚石,甚至死亡。于是有了上帝与朝圣者,有了伯爵与吸血鬼,有了天使与加百利,有了恶魔与路西法。
开膛手杰克的枪口窜出轻烟淡淡,世界不相信,世界。
她也念《古兰经》,她也信伊斯兰,她也用没有重低音炮的音响放摇滚,她也在看悲情肥皂剧时吃苍蝇小店送来的快餐。她同样也会反复诵读爱人的名字,再簇上前闻闻花开的静然。
喜欢青色,那种生机盎然的颜色,牵着时间万物的消长,奔赴一场奭大的死亡。
寂寞挡在眼前如横亘,夭夭冶用灰色作光芒。她翘着腿撅着嘴路过那些灵敏而平凡的生命时,她会骄傲地仰起脸。他是英雄。他是我丈夫。
他是英雄。硬扯着烟缁色的笑容,勇猛地用身体抵抗,抵抗了些什么,也许不过是心中一些幼稚而纯洁的幻想。他听见风呼啦啦地吹,遍体鳞伤地穿过荆棘,于是他便拿自己的身体,呼啦啦地强穿敌人的炮火封锁线。
风遍体鳞伤,他也遍体鳞伤。
风长啸一声,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狂奔,他也长啸一声,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狂奔。
他不是风。所以风穿透了敌人的铠甲,而他,必须倒下。
烈士铭碑上他的名字排在榜首,她微笑,然后泪如雨下。
这便是他承诺给她的整个世界,用名誉,和血。
盛唐之时不允许有这样的嗜血魔,道家的地方独裁渐渐被人们憎恨,她也再没见过莲。她常常会想那个如此气傲的家伙是不是还会站在巨马上,斗篷翻飞,瞳中燃起焚烧三界的红莲之火,那样纯粹,那样悲悯。所过之处,皆为修罗场,腥涩的甜味铺天盖地散开去,无边无际。
亦无法无天。
想到这里她会吃吃地笑,莲不是这般恶魔的人罢,呵呵,这是不是自己梦中的自己呢?
她一直便不喜欢女儿身,她想成为男儿上阵,燕然勒功,然后醉尸沙场,从此酣睡在被血液浸湿的土地上,看飞扬的旌旗如何如何华美,也看闪光的旄钺如何如何锋利,看摇摆的马鬣如何如何狭长。
有时她会痛恨自己为什么这么血腥,于是裹一身黑氅佯装黑无常,拿起铁索,撇下八字眉,用死亡代替一切语短言长。
笑声如银铃,她说,我只是想离开。
或问,去哪里?
答曰,奔赴幕上梦想。
“出鞘剑,杀气荡,风起无月的战场。
千军万马独身闯,一身是胆好儿郎。
儿女情,前世帐,你的笑活着怎么忘。
美人泪,断人肠,这能取人性命是胭脂烫。”
拾阶而上,裙裾上盛开大朵大朵的珍珠和年华,发迹垂下几斛琅玕,几迭团扇。
“诀别诗,两三行。
写在三月春雨的路上,若我能,遇见莲以前,她只会抚琴微笑。她不会弹琴,她甚至分不清哪一个是商音。站在台上唱那些自说愁的歌曲,穿着华贵的衣裳,摆弄自己的肢首。如此冷漠微寒的衣袂,躲藏在这堂皇的景色中,格格不入,的孤独。
还未及笄,心便已开始老去。
遇见莲那天,她恐惧地不知所措。莲站在高大的棕色宝马上,穿着饱满的黑色灯笼裤,黑色短马甲,黑色护腕,黑色布鞋,黑色的斗篷被风吹扬,黑色的瞳孔啸成剑气,黑色的发乱成不羁的形状。她从未见过这么轻视死亡的人,而莲,是第一个。反着光的马孙刀颀长,将生命分成过去和现在两段,轻易地刺死了生命的未来。
鲜血溅起来,乱发下莲的笑容,那样意气风发。
那一刻,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变成那马孙刀下起舞的亡魂,在最近的距离看清莲嘲讽般的笑容,散发着毁灭世界的诡异气息,又洋溢着救世主般的孤傲,和居高临下。
莲看她时是居高临下的,马孙刀挑起她的下颔,刀刃清澈反射出她下颔的轮廓,划过时切断她耳旁落下的碎发。
从那一刻开始她如此地讨厌自己。莲皱着眉,鄙夷地说:“女人。”
她本来也是不喜欢女人的,她也希望自己是个男儿身。而这两个字冰冷得打掉她所有生存的臆想,深沉而且,绝望。
道莲。她念这两个字时很用力,少年回头,看不见她藏在阴影中的表情。
凯达格兰大道上教堂传出虔诚的歌声,唱诗班的孩子穿素色的衣服,闭眼着赞颂上帝。纯色皮肤上朵朵天真,张眼眸子里写满沧桑。
是不是会有面包和方糖,和着咖啡在阳光慵懒的午后,细享?而又要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“人”,是不是必须像该隐一样站起来挥舞盾和长枪?甚至无法透析生命的目的,是不是只为刺穿空气上端暧昧不清的欲望?
没有人回答,亦没有人听到我的声响。
白鸽被工业浓厚的气味熏得灰黑,飞行中只有眼睛像鸢尾花的光芒。咽下的是希望,曲水流觞。
心中的皱褶似蝴蝶,为了谁,折了翼。
那样一个似幻非幻的世界,所有烟火都踏在历史的纹理中,人们在梦中惊魇或深呓,没有什么可以成为阻止时间前进的绊脚石,甚至死亡。于是有了上帝与朝圣者,有了伯爵与吸血鬼,有了天使与加百利,有了恶魔与路西法。
开膛手杰克的枪口窜出轻烟淡淡,世界不相信,世界。
她也念《古兰经》,她也信伊斯兰,她也用没有重低音炮的音响放摇滚,她也在看悲情肥皂剧时吃苍蝇小店送来的快餐。她同样也会反复诵读爱人的名字,再簇上前闻闻花开的静然。
喜欢青色,那种生机盎然的颜色,牵着时间万物的消长,奔赴一场奭大的死亡。
寂寞挡在眼前如横亘,夭夭冶用灰色作光芒。她翘着腿撅着嘴路过那些灵敏而平凡的生命时,她会骄傲地仰起脸。他是英雄。他是我丈夫。
他是英雄。硬扯着烟缁色的笑容,勇猛地用身体抵抗,抵抗了些什么,也许不过是心中一些幼稚而纯洁的幻想。他听见风呼啦啦地吹,遍体鳞伤地穿过荆棘,于是他便拿自己的身体,呼啦啦地强穿敌人的炮火封锁线。
风遍体鳞伤,他也遍体鳞伤。
风长啸一声,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狂奔,他也长啸一声,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狂奔。
他不是风。所以风穿透了敌人的铠甲,而他,必须倒下。
烈士铭碑上他的名字排在榜首,她微笑,然后泪如雨下。
这便是他承诺给她的整个世界,用名誉,和血。
盛唐之时不允许有这样的嗜血魔,道家的地方独裁渐渐被人们憎恨,她也再没见过莲。她常常会想那个如此气傲的家伙是不是还会站在巨马上,斗篷翻飞,瞳中燃起焚烧三界的红莲之火,那样纯粹,那样悲悯。所过之处,皆为修罗场,腥涩的甜味铺天盖地散开去,无边无际。
亦无法无天。
想到这里她会吃吃地笑,莲不是这般恶魔的人罢,呵呵,这是不是自己梦中的自己呢?
她一直便不喜欢女儿身,她想成为男儿上阵,燕然勒功,然后醉尸沙场,从此酣睡在被血液浸湿的土地上,看飞扬的旌旗如何如何华美,也看闪光的旄钺如何如何锋利,看摇摆的马鬣如何如何狭长。
有时她会痛恨自己为什么这么血腥,于是裹一身黑氅佯装黑无常,拿起铁索,撇下八字眉,用死亡代替一切语短言长。
笑声如银铃,她说,我只是想离开。
或问,去哪里?
答曰,奔赴幕上梦想。
“出鞘剑,杀气荡,风起无月的战场。
千军万马独身闯,一身是胆好儿郎。
儿女情,前世帐,你的笑活着怎么忘。
美人泪,断人肠,这能取人性命是胭脂烫。”
拾阶而上,裙裾上盛开大朵大朵的珍珠和年华,发迹垂下几斛琅玕,几迭团扇。
“诀别诗,两三行。
写在三月春雨的路上,若我能,遇见莲以前,她只会抚琴微笑。她不会弹琴,她甚至分不清哪一个是商音。站在台上唱那些自说愁的歌曲,穿着华贵的衣裳,摆弄自己的肢首。如此冷漠微寒的衣袂,躲藏在这堂皇的景色中,格格不入,的孤独。
还未及笄,心便已开始老去。
遇见莲那天,她恐惧地不知所措。莲站在高大的棕色宝马上,穿着饱满的黑色灯笼裤,黑色短马甲,黑色护腕,黑色布鞋,黑色的斗篷被风吹扬,黑色的瞳孔啸成剑气,黑色的发乱成不羁的形状。她从未见过这么轻视死亡的人,而莲,是第一个。反着光的马孙刀颀长,将生命分成过去和现在两段,轻易地刺死了生命的未来。
鲜血溅起来,乱发下莲的笑容,那样意气风发。
那一刻,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变成那马孙刀下起舞的亡魂,在最近的距离看清莲嘲讽般的笑容,散发着毁灭世界的诡异气息,又洋溢着救世主般的孤傲,和居高临下。
莲看她时是居高临下的,马孙刀挑起她的下颔,刀刃清澈反射出她下颔的轮廓,划过时切断她耳旁落下的碎发。
从那一刻开始她如此地讨厌自己。莲皱着眉,鄙夷地说:“女人。”
她本来也是不喜欢女人的,她也希望自己是个男儿身。而这两个字冰冷得打掉她所有生存的臆想,深沉而且,绝望。
道莲。她念这两个字时很用力,少年回头,看不见她藏在阴影中的表情。
凯达格兰大道上教堂传出虔诚的歌声,唱诗班的孩子穿素色的衣服,闭眼着赞颂上帝。纯色皮肤上朵朵天真,张眼眸子里写满沧桑。
是不是会有面包和方糖,和着咖啡在阳光慵懒的午后,细享?而又要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“人”,是不是必须像该隐一样站起来挥舞盾和长枪?甚至无法透析生命的目的,是不是只为刺穿空气上端暧昧不清的欲望?
没有人回答,亦没有人听到我的声响。
白鸽被工业浓厚的气味熏得灰黑,飞行中只有眼睛像鸢尾花的光芒。咽下的是希望,曲水流觞。
心中的皱褶似蝴蝶,为了谁,折了翼。
那样一个似幻非幻的世界,所有烟火都踏在历史的纹理中,人们在梦中惊魇或深呓,没有什么可以成为阻止时间前进的绊脚石,甚至死亡。于是有了上帝与朝圣者,有了伯爵与吸血鬼,有了天使与加百利,有了恶魔与路西法。
开膛手杰克的枪口窜出轻烟淡淡,世界不相信,世界。
她也念《古兰经》,她也信伊斯兰,她也用没有重低音炮的音响放摇滚,她也在看悲情肥皂剧时吃苍蝇小店送来的快餐。她同样也会反复诵读爱人的名字,再簇上前闻闻花开的静然。
喜欢青色,那种生机盎然的颜色,牵着时间万物的消长,奔赴一场奭大的死亡。
寂寞挡在眼前如横亘,夭夭冶用灰色作光芒。她翘着腿撅着嘴路过那些灵敏而平凡的生命时,她会骄傲地仰起脸。他是英雄。他是我丈夫。
他是英雄。硬扯着烟缁色的笑容,勇猛地用身体抵抗,抵抗了些什么,也许不过是心中一些幼稚而纯洁的幻想。他听见风呼啦啦地吹,遍体鳞伤地穿过荆棘,于是他便拿自己的身体,呼啦啦地强穿敌人的炮火封锁线。
风遍体鳞伤,他也遍体鳞伤。
风长啸一声,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狂奔,他也长啸一声,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狂奔。
他不是风。所以风穿透了敌人的铠甲,而他,必须倒下。
烈士铭碑上他的名字排在榜首,她微笑,然后泪如雨下。
这便是他承诺给她的整个世界,用名誉,和血。
盛唐之时不允许有这样的嗜血魔,道家的地方独裁渐渐被人们憎恨,她也再没见过莲。她常常会想那个如此气傲的家伙是不是还会站在巨马上,斗篷翻飞,瞳中燃起焚烧三界的红莲之火,那样纯粹,那样悲悯。所过之处,皆为修罗场,腥涩的甜味铺天盖地散开去,无边无际。
亦无法无天。
想到这里她会吃吃地笑,莲不是这般恶魔的人罢,呵呵,这是不是自己梦中的自己呢?
她一直便不喜欢女儿身,她想成为男儿上阵,燕然勒功,然后醉尸沙场,从此酣睡在被血液浸湿的土地上,看飞扬的旌旗如何如何华美,也看闪光的旄钺如何如何锋利,看摇摆的马鬣如何如何狭长。
有时她会痛恨自己为什么这么血腥,于是裹一身黑氅佯装黑无常,拿起铁索,撇下八字眉,用死亡代替一切语短言长。
笑声如银铃,她说,我只是想离开。
或问,去哪里?
答曰,奔赴幕上梦想。
“出鞘剑,杀气荡,风起无月的战场。
千军万马独身闯,一身是胆好儿郎。
儿女情,前世帐,你的笑活着怎么忘。
美人泪,断人肠,这能取人性命是胭脂烫。”
拾阶而上,裙裾上盛开大朵大朵的珍珠和年华,发迹垂下几斛琅玕,几迭团扇。
“诀别诗,两三行。
写在三月春雨的路上,若我能,
标签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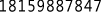 邮箱:
邮箱: